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文章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不用于商业用途,仅为学习交流之用,如文中的内容、图片、音频、视频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本站站长删除。
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知识产权家】
孙远钊 美国亚太法学院研究院执行长 暨南大学特聘教授 本刊专栏作家
“中国知网”(简称“知网”)近来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在展开相关讨论之前,约25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几起事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反思的教训。
一场内容数字化的鏖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类正式进入了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时代。作为最具指标性的新闻报业单位,《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高管层已然认识到,未来将是以数据化的新闻和评论出版为主的市场。于是,《纽约时报》与两个颇具知名度的数据库厂家(如“律商联讯”NexisLexis®等)签约,将该报历史上的所有内容全部数字化,并提供线上检索服务(需要付费,且费用不低),也制作成光盘出售。这些数字化内容包括了由27000余名自由作家(freelancers,不是《纽约时报》的正式雇员)撰写的文章。《纽约时报》在上述协商、订约的过程之中,从来没有同这些作家或其隶属的作家协会(工会)打过任何招呼,从付费检索服务获得的收益,也自然悉数进了报社的口袋。
自由作家们当初通过作家协会的集体协商与《纽约时报》签约时,完全是以传统实体的纸本报纸为基础,根本未曾触及内容数字化与相关的电子档案的处理问题。眼看报社又开辟了新的收益渠道,却把他们全给晾在一边,自然十分不快。于是,全国作家工会(National Writers Union)的时任会长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 B. Y. Tasini,下图)牵头,联合其他5名作家共同起诉《纽约时报》和另外5家媒体与数据库公司,主张其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他们从1990年到1993年之间撰写的文稿,构成著作侵权。被告则抗辩,报纸一经刊登,就构成了对原来个别作品的改编(revision),并组合成为了一个演绎或派生的汇编作品(collective works),出版者也就享有汇编著作权,因此自然可以自由地从事对其中内容的处置,不需要再经过原作者的同意。该案件在初审时原告败诉[主审法官是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有史以来首位拉丁裔女性大法官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M. Sotomayor)],但之后,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判决,继而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再审。全案的争议焦点是:“汇编著作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的范围及于何处?该权利与各个单篇文章原作者的著作权的关系如何?

Jonathan B. Y. Tasini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认定,判决共同被告《纽约时报》等构成侵权。在解释美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的含义时,法院表示,被告出版商无法用汇编著作权来覆盖其整个数据库当中的所有作品,因为根据使用者的检索要求,数据库从事了对个别单篇作品(而不是连同整个上下文)的复制和发行。由于被告把数据库比作“电子图书馆”,法院也就借此指出,当使用者想要检索某篇文章时,数据库提供的并不是含有该文章的整份报纸或特定的期刊,而是直接抽取并复制、发行了特定的单篇文章,这就完全超越了其本身汇编著作权的范围。换句话说,通过该判决,法院明确了汇编著作权的范围仅及于有汇编者贡献的独创表达部份,包括最终呈现的筛选、编排、组织与排列,别无其他。
经过8年艰苦的司法鏖战,这一判决犹如宣告了“大卫战胜歌利亚”式的奇迹。然而,就在自由作家们还来不及庆祝时,《纽约时报》就祭出了杀手锏:其准备把和本案相关的,之前与《纽约时报》没有订立许可合同的27000余名作家从1980年到1995年的115000多篇文章悉数从其数据库中删除。按该报时任发行人兼董事会主席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下图)的表述,《纽约时报》“现在要采取艰困且伤感的程序,从历史性的电子文档中把相当一部份移除”。其他的一些出版商,如《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等为了避免法律风险,也纷纷跟进,准备采取类似的行动。

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些后续发展几乎都被撰写本案反对意见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完全预料到了。他在意见书里表示,“鉴于寻觅个别自由作家的困难与遭到法定赔偿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会产生强迫电子文档系统从数据库中清除自由作家作品的后果。”他还预料多数意见的判决不会带给自由作家们任何额外的实质性财务收益。他在反对意见书中摘录了由著名制片人肯·伯恩斯(Kenneth L. Burns)具名提呈的“法院之友”书状(amicus curiae brief)当中的一段文句:“从电子典藏中删除这些材料,无论是基于任何理由抑或仅是一个偶发的原因,大规模的删除都将破坏电子档案对历史研究者所能提供的最主要效益——功效性、正确性和完整性。”
虽然主笔多数意见判决书的露丝·贝德尔·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J. Ruth Bader Ginsburg)也意识到了判决可能会产生的后遗症,她依然认为必须在法言法,况且,这样的极端结果未必真会发生;即使真有窒碍难行的问题,各方当事人或可通过谈判协商达成某种妥善安排;国会也可考虑通过立法,对这类作品的许可、复制、发行和相关费用的配置等事宜给出必要的指引。
《纽约时报》方面也不是埋头硬干。他们自是十分明白,无论该案争议最终如何解决,将来报纸的许多版面还是必须依赖这些自由作家的稿件来填充。因此,没有必要在输掉了官司之后还要继续作绝,以避免在社会上留下恶劣的形象,破坏自身长期积累的名声。所以,在正式动手删除档案前,《纽约时报》给自由作家们开设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和电话热线,只要自由作家们自愿同意签署一项协议,给予《纽约时报》全球范围的非独占许可,就可以避免作品遭到删除的命运(这也意味着《纽约时报》无须再行支付任何额外的许可费)。最终,约有20%的自由作家选择接受了这一条件。至于《时代杂志》完全没有采取类似的做法,就直接从数据库当中删除了可能构成侵权的文档。
《纽约时报》的上述做法,无疑是绵里藏针的高招,同时兼顾了面子和里子。明明是败诉方,却以删除档案为筹码和杠杆,不声不响地化被动为主动,反而让获得胜诉的一方几乎完全陷于被动。至于塔西尼本人和其他不愿屈从的自由作家们,则从2001年9月10日开始便在《纽约时报》总部前打算进行长期性的抗议活动,并准备呼吁罢工,威胁让报纸的多个版面“开天窗”。不料,第二天上午,纽约市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于是塔西尼等人的计划不得不顺延到翌年1月2日,但已势成强弩之末。《纽约时报》虽然曾与这些“鹰派”作家们进行过象征性的协商,但整个协商进程极度迟缓,自由作家只能选择接受报社开出的条款,或坐视自己之前贡献过的文章从电子数据库当中完全清除。
本案中,6位自由作家在诉讼中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战役”,获得了象征性的胜利,但却因此让自己和后来的自由作家们输掉了整个“战争”,情况反而比起诉之前变得更差了。现在,任何想向《纽约时报》投稿的自由作家,从一开始就必须签署一份“职务创作协议”,从而完全失去了在合同期间内对自己未来作品的控制权,自然也就失去了更多的获得收益的渠道,因为他们将不再能把自己的作品分享给其他的媒体同时或后续刊登。《纽约时报》则是最大的赢家:其不仅不需要支付任何正式职员的常态性薪资与社保、退休金等额外支出,还获得了完全等同的文稿贡献,甚至是独家报道或评论,更可从电子检索中获得额外的收益,而无须分享给原作者。塔西尼后来也因此和其他一些原因而黯然下台。后来,塔西尼成为民主党的选举顾问,并两度协助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参议员竞选总统。
但是,该案中真正的最大输家,恐怕是著作权法制和社会公益。法院依法论法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其给出的法理说明也无懈可击。但是这样的推导却正好产生了著作权保护体系制定之时最不乐见的结果,不但再次显示了法律的局限性,也让本来寓含重要公益意义的数据库价值受到了相当的减损,更与著作权法保护文化资产与创意的本意背道而驰。
不过,就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出台后不久,受到该判决的鼓舞,作家协会(Authors Guild)、美国新闻从业人员与作者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Journalists and Authors)、全国作家工会等联合超过3000名自由作家,共同起诉了《纽约时报》、道琼公司(Dow Jones,《华尔街日报》的所有者)、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奈特·里德报业集团(Knight Ridder)、里德·爱思唯尔出版公司(Reed Elsevier PLC)等主要媒体和数据库提供者对60万篇作品构成侵权。这场集体诉讼的真正目的,无非是给出版方加大压力以促使达成和解。然而,双方的谈判一共拖延了17年,最终于2018年4月达成了协议,由出版方一次性赔付9400万美元,并负担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由于每位作家的情况并不相同,其中一些人从未申请版权注册,所以,最后分配到每位作家的赔偿金额的计算过程极为复杂,不同作家获得的赔偿金额彼此也有很大的差异。
另一场鏖战与“载体中立”法则
同样受到“塔西尼案”的影响,18位曾经在《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刊载作品的自由作家和摄影师联袂起诉该杂志的主办者国家地理学会和尹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 Co.),起因是被告计划将该杂志自1888年创刊号开始的所有内容数字化,并制作成光盘出售,即《国家地理完整版》(The Complete National Geographic)。显然,该案中,被告事前也完全没有知会独立作家和摄影师们,更遑论支付额外的费用。
与“塔西尼案”不同,《国家地理完整版》采用电子扫描方式制作,用户从屏幕上可以看到与该杂志原始纸本完全一样的文字、图像和内容,并按月纪年依序排列。换言之,光盘版对于原始版本的内容、编排、格式或表现等都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审理本案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表示,虽然被告在新的汇编作品(光盘)当中增加了一些实用性的功能,但只要这些附加的事物或功能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原始汇编作品(纸本杂志)的完整性,便还在著作权法“容许改编”(permissible revision)的范围之内,符合“载体中立”(media neutrality)的要求。法院因此判定,《国家地理完整版》没有对自由作家和摄影师的原始作品构成侵权。
由于“塔西尼案”和该案的判决,“载体中立”已成为出版商保全和行使其汇编著作权的重要原则。将书面(纸本)转换为电子格式时,如未对其中的各个原始作品造成任何本质性的变更,则出版商可以主张适用“容许改编”来运用其本身的汇编著作权。无论如何,将一个版面中的个别作品单独抽取使用,都会被法院视为构成了本质性的改变;该行为如果未经事前许可,便构成侵权行为。
知网引发的问题
知网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引发的问题主要有四:
其一,知网所收录的大量期刊文献,其中究竟涉及哪些权利,归属于谁?
其二,如果知网不拥有著作权,其是否取得了合法许可?抑或构成合理使用?
其三,知网提供的文献查重功能不对个人开放,是否构成滥用垄断地位?
其四,知网案件的损害赔偿与后续整改措施应如何确定?这对知网的长远发展有何影响?
著作权存在与否及其归属
有调研显示,自2004年同方知网(北京)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以来,由该公司拥有和运营的“中国知网”与其分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以下统称“知网”)已先后经历超过1500起诉讼,其中至少有1100多起涉及著作权归属或侵害原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知网提出的主要抗辩包括:(1)其已经取得了期刊的许可(“独家授权”),将历来在期刊上刊载过的文献悉数汇编收录到自身数据库和相关产品之中,并“通过光盘、网络、手机登载体进行出版发行,提供信息服务”;(2)其享有对期刊的汇编著作权;(3)纵使其权利不及于各个单篇的原始作品,其数据库或电子期刊仍可适用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规定,不经作者许可而从事使用(即合理使用)等。值得注意的是,据“知网”自身的表述,其数据库通常与学校或期刊合作,不与作者直接对接。换句话说,作者在向期刊投稿时,就应看到投稿须知中的“稿件将编入知网数据库”等表述。
截至目前,不同的法院都没有接受或支持上述抗辩,导致知网迭遭败诉。不过,由于个案的损害赔偿金额相对有限,所以频繁败诉对知网的整体运营收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一经判决败诉,知网便会立即把涉案的相关电子文档悉数从其数据库中删除,反而让原作者的文献无法呈现或被检索到。由此可见,不分国界,也无分国情,知网的反应和行动与前述《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律商联讯数据库等几乎完全一致,但由于知网目前是中文学术文献查阅领域使用范围最广的服务提供者,相关案件也就寓含了更大的公益因素,知网数据库的质量、内容势将对研发创新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与域外或国际间的规定基本一致。再综合梳理中国法院历来对知网的论述和认定,至少可得到两点结论:其一,知网将涉案文章收录并提供下载服务,不属于期刊与期刊之间的转载或摘编行为,因此不适用《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知网无法主张其构成“法定许可”;其二,每一期刊在文章的选择、编排方面如体现出一定的独创性,即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汇编作品,无论是否征得被汇编文章作者的许可,其著作权均由汇编者享有,汇编者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汇编作品,但其范围不及于也不涵盖各单篇文献的原始著作权。换句话说,除非另有证据,知网对单篇文章并没有任何著作权。
著作权的使用许可
《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对于知网或其转载来源的期刊杂志社经常仅通过单方、制式性的声明主张享有各单篇文献原作者的著作权的做法,目前学界的观点与法院的判决相当一致,即均认为无法仅据此便认定期刊已经取得了著作权或是有效的使用许可。
例如,在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与知网的论文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刊载作者论文的期刊仅凭格式化、概括性的声明或协议,在既没有作者的签字确认,原作者亦不认可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原作者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让给期刊杂志社,即无法认定刊载论文的期刊杂志社取得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与知网签订数字出版合作协议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知网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原作者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学界观点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李琛教授对知网以单方声明取得原作者著作权持非常保留的观点:“综合判断作者有无许可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允许期刊社转授权的意思表示〔,〕如果无法明确作出这种推断,应作有利于作者的解释。……即使声明的内容非常清晰,考虑到期刊社的声明属于格式条款,在当前的科研考核体制之下,作者处于弱势,如果结合授权范围、报酬数额等因素判断声明的条件明显违反公平原则,要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九十八条检验其是否无效或应作有利于作者的解释,而不能当然地认可声明的效力。”
中国政法大学刘文杰教授也认为:“著作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除外情形主要是指著作权法中有关法定许可及合理使用的规定。杂志社的单方声明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投稿作者可能并不知晓,二是声明内容模糊宽泛。而根据著作权法第29条的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实际上,著作权法不但要求就作品使用订立许可合同,还要就许可事项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杂志社的单方声明很难满足这些要求。换言之,杂志社若要从作者处取得信息网络传播的授权或者转授权的权利,应当与作者订立合同,同时,授权条款应当公平合理。”(按,刘教授在此显然是把“授权”和“许可”两个名称交替使用。)
然而,知网在其网站上的“版权声明”却仍然从一开始便表示,“中国知网的全部内容均已获得权利人的授权”,非常可疑。无论如何,知网案与前述的美国“塔西尼案”等固然在具体事实方面有所不同,但最终都涉及期刊与数据库提供者无权处分汇编作品中个别单篇文献作品的问题,知网案也产生了与“塔西尼案”同样的困境:既然被告被判决构成著作侵权,那么理应立即删除或销毁相关侵权;涉及电子档案时,把相关侵权物从数据库中移除,也属天经地义,是维权执法的主要目标之一,无可厚非;然而,这样的处置却显然与社会公益和著作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宗旨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不良后果,也让知网陷入了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两难困局。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是,如果知网如同前述的《国家地理杂志》案一般,将原纸本期刊的整体排版予以扫描、制作成电子档案,并收录到其数据库,是否有可能因“媒体中立”法则而得以免除侵权责任?对此问题,目前尚无司法判决或解释可为依循,但鉴于知网重大的公益性,这或许可作为知网未来整改的一个方向。
知网是否构成滥用垄断地位
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以下两个环节:
第一,知网采取被媒体称为“借鸡生蛋”的运营与盈利模式,即一边通过期刊杂志出版单位直接收录著作权人作品,另一边在未明确获得作者本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传播、供使用者下载以获利,而文献作者却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报酬,甚至连下载自己的作品都还需付费。在此,知网是否构成滥用垄断地位?
第二,知网提供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通称“论文查重”服务)之前一直只提供给其指定的机构(非自然人会员)使用,未对个人用户开放(2022年6月12日已经宣布开放,但仍须收费)。鉴于“查重”已经成为当前所有高校教师、学生等必须使用的工具,于是相关使用者通常只能通过学校图书馆并缴纳一定费用后才能获得此一查重服务。在此,知网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对于上述第一个环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于2022年5月13日正式立案调查。对于上述第二个环节,则是有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郭兵于2021年12月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起诉知网,指控其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三)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规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1日正式受理此案。
由于上述两案还在进行当中,社会各界也已经提出了相当多的讨论,本文拟提出以下四个问题,以期集思广益:
其一,举证要求与责任配置问题。假定知网的相关市场的定义和范围,是面向中国境内的在线论文数据库服务市场(包括检索、上传与下载和其他的周边服务,如“查重”功能等)。知网从一开始便是在行政特许的保护伞下形成独特的市场垄断地位,其在掌握与汇集绝大多数的信息方面都遥遥领先,诸如万方、维普等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数据库都难以望其项背(姑不论是否取得合法的著作权许可)。参酌拟议中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滥用规定》(草案)),知网所谓“借鸡生蛋”的运营与盈利模式本身是否符合《滥用规定》(草案)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其第22条?需要达到如何的举证要求与标准?应由何方来承担举证责任?法院或执法机构是否可以迳行推定相关事项?
其二,促进竞争与利益平衡问题。鉴于在线论文数据库服务市场寓含重要的公益色彩,一旦导入利益平衡要求,是否会与促进竞争产生竞合;特别地,这是否会与“使用者付费”的基本原则冲突?亦即,如果真正贯彻《反垄断法》的精神,同时鼓励竞争与合法许可使用他人的著作权,是否将导致知网面临拆解的结果,使得使用者至少在相关市场重新调整的期间内面临相当的不便,无法从单一或主要来源获取所需的检索结果,显著增加相关的检索时间、费用等各项成本,降低检索结果的质量?
其三,单方设限与滥用垄断问题。《反垄断法》是为了规制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而设,以间接保护消费者的福祉或经济利益。知网从一开始就未将其论文查重系统或功能直接向个别的使用者(自然人)开放,仅此单一的举措是否足以构成“滥用垄断地位”?由于以往个人使用者依然可以通过单位或机构的账户获得查重服务,其他的竞争者也提供了类似的功能,有无任何的实证调研显示知网开放查重服务给个别使用者将导致促进竞争的结果,抑或强化知网的垄断地位的结果?
其四,论理(合理)分析或当然违法问题。参考域外和国际间的立法与实践,检测被告是否从事了排斥性的行为时,一般采用所谓的“举证转换框架”(burden-shifting framework),或“合理分析”或“论理分析”(rule of reasons)法则,亦即主张权益受损的原告首先必须通过初步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证明被告的行为产生了反竞争效果,而后举证责任便转换至被告,被告可提出反证证明其行为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如果在此阶段,反证无法成立,原告便获得胜诉;如果反证能够成立,举证责任就再次转移到原告,原告必须举证被指控行为所造成的反竞争效果超过了其促进竞争所能带来的利益。在知网案中,是否需要以此种更为细致的方式、更加复杂的经济模型与分析来进行交叉比对,抑或简单套用法律条款即可?何者更为妥当?
此外,即使直接套用现行《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三)项(或将来的第二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如前所述,由于知网过去从来没有对个人直接开放使用其查重系统,这是否仍然构成“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查重功能是否算是“交易”?这里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商榷、研究之处。如果对于《反垄断法》的上述条款采取广义或扩张解释,是否可能反而产生阻碍创新的后果,导致厂家为了避免法律风险而放弃对新功能、新服务的开发,削减消费者或社会大众的福利?
结论
数据检索已成为当今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确保数据库,尤其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研究系统的功效性、正确性和完整性,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信建设工程。
伴随其本身创立的特殊背景和长年以来收录文献的“擦边球”手法,知网形同“空手夺刀”,以买空卖空、慷他人之慨的方式赚取高额的利润,坐上了当前中文在线论文数据库服务市场的龙头位置。然而,不计其数的著作侵权纠纷,证明了这个看似庞大的数据库实际上可能只是虚有其表的一座“纸牌屋”,欠缺最起码的合法著作权基础。此外,因牵扯论文检索的重要社会公益,知网实际上织出了一张让自己与法律都难过的网,其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相互纠结、彼此冲突,无论如何处理,都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此类问题无法依靠法律完全妥善地解决,这再次凸显了法律的局限性。
固然知网已经“从善如流”,和赵德馨教授达成了谅解与协议,把原先撤除的赵教授的文章悉数重新放回相关数据库,但该事件引发的各项根本性问题却仍悬而未决。例如,其他获得胜诉却依然遭到文章下架的原告又复如何?如果恢复其涉案文献,固然满足了社会公益的需求,但纯粹就法论法,实际上造成了知网继续侵权的结果,对此又应该如何处置?显然,这些难题已无法纯粹依靠法律解决。至于反垄断的调查和诉讼,就更需要极度谨慎处理,尤其需要依靠详尽可靠的实证调研与经济分析。牵一发可动全身,知网案所牵涉的不仅是知网一家的问题,而是未来整个数据库产业的发展。
归根结底,知网案引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各方协商以妥善处理,必须避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将该事件导向零和博弈,避免任何一方“赢得战役却输掉战争”的结果。对此,美国的“塔西尼案”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负面教训!
[28]例如,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院杨勇认为,“若知网高价向高校销售数据库,通过“降评级”“下架论文”等措施“迫使”期刊授权,涉嫌违反该条第1项规定;知网拒绝向个人提供查重服务涉嫌违反第3项规定。然而,杨勇却没有展开其论证过程,颇为可惜。参见杨勇,浅析论文查重和下载服务的法律规制——从知网涉垄断行为调查谈起,《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22年5月23日,载于《网舆勘策院》网站https://mp.weixin.qq.com/s/dHltoAKvRO_JN6o87Htz4g。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第18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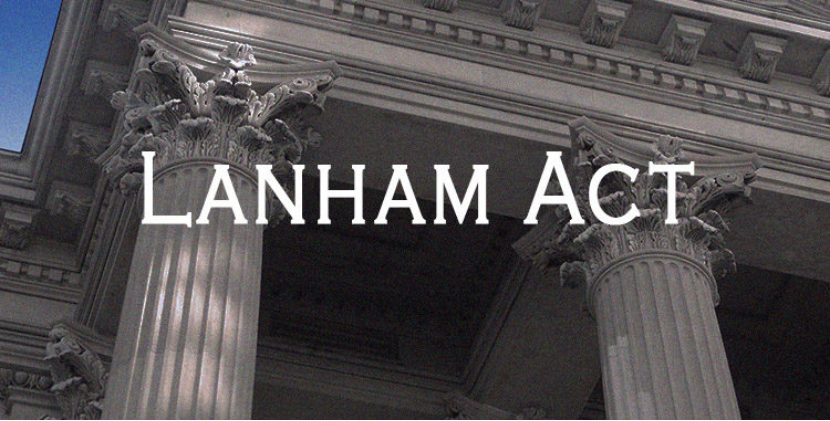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